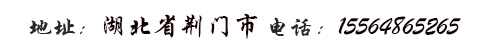牛排和螺旋起草器
|
文并摄影/天冬绘图/林雨飞 “喂喂,这么着可不行!我来教你!” 在阿尔卑斯山中一家小餐馆里,老猎人咔哒咔哒走过来,和我说起了用餐礼仪。说是老猎人,实则此人乃是小餐馆的经营者,餐馆以野味著称。之所以有野味出售,是因他本身持有狩猎许可。在秋日的狩猎季里头——仅两个星期而已——按照规定的份额,猎得马鹿啦岩羊啦羚羊啦(倒是当叫做臆羚),兽皮鞣制妥当,挂在餐馆的墙壁上,肉则腌制起来。 然而打一开始,老猎人就似乎对我抱有成见。哪来的成见不清楚,或许因我吃蘑菇过敏,不能享用他的值得夸耀的蘑菇酱炖肉,抑或是我自进得餐馆以来,即以相当随意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头。“什么呀,那人!活脱脱一摊果冻!以这等姿势坐在餐桌前,莫不是瞧不起我这小餐馆不成?”总之原因并不知晓,但老猎人不喜欢我,这点多少看得出。 头盘撤下之时,因我的餐刀和叉子随意放在盘子里头,老猎人便上前说教起来。“这么着可不行!喏喏,若是吃完了,刀和叉子要摆放在右手边。此乃用餐礼仪,能懂?”说罢,大约是觉得如此说教亦有些过火,老猎人不无勉强地笑笑,说道:“唔,在中国不常用刀和叉子吧?我知道,中国有万里长城,可是没有岩羊。” 诚哉斯言,在中国我是不常用刀叉,西餐礼仪也委实抱歉。然而此地并非意大利或法国的高级餐厅,在山里头淋着雨走了一整天,我是再无余力,应付什么用餐礼仪了。继而主菜端了上来,乃是用酸滋滋的红酒腌制的极咸的鹿肉。别人倒是在吃蘑菇酱炖肉。坐在我对面的亮君,仅以右手拿着叉子,对付盘里的主菜。管他什么劳什子的用餐礼仪呢! 此后我才知晓,非但炖肉,通心粉也罢,焗蔬菜也罢,烤鱼啦牛排啦,这个那个,亮君无不以一把叉子将其统统解决。一如海皇波塞冬。我到底知晓应当左手持叉,右手持刀,左右弄错固然时而有之,但不借助两把餐具,总难将食物处理妥当。若是不用牛排刀,何以将肉撕裂成足以吞咽的大小呢?反正亮君以叉子和牙齿就能做到。盘子里头空空如也,刀却从未碰过。 有一次用错了刀来着。侍者误将面包刀当作了牛排刀,以此切肉的感觉,唔,大约如同火烈鸟穿着弄错尺码的雪地靴,趟过阿拉斯加冷冰冰急嗖嗖的溪流。“不好意思,牛排刀在这里!”侍者将正确的刀送来时,亮君已然将牛排吃掉了一半。一把叉子足矣。此等技能令我由衷钦佩。 “中国人嘛,有筷子就行啦!”谈及此事时,有人故作轻松地对我说,“喏,叉子和筷子,终究差不多,不觉得?”觉不觉得姑且不论,亲自一试便知,仅用一把叉子吃上十天西餐,怕是够受的。 挑选适宜的工具,从前我是不甚在意。“能用就行了嘛,何苦花上五倍十倍的价钱,去买个什么专用工具呢?”毕竟也不至于天天吃牛排,面包刀固然不够称手,买上一把牛排刀放在家里头,总觉得有些小题大做。牛排刀用不上,雪地镐用不上,为六弦琴调音之用的音叉也用不上。然而一旦开始亲自动手种花,工具之事就不得不认真考量。 为地面翻土时,拿着看似精巧的迷你铲,注定一事无成。不骗你,那些迷你园艺工具,大都是为了小孩子胡乱玩上一把,或是为了拍照时看似美妙而存在的。少许做旧的铁质铲子,刷着复古的蓝黝黝的外漆,木质手柄的花纹满怀考究感,但这玩意儿归根结底,连一点土块儿也挖不动。小孩子拿去海边挖沙子自是够用,但反正我手持此等迷你铲,长叹一声,决定去买切实可用的工具。 这么着,看似粗犷的大铲子也有了,沉甸甸的锄头也有了,翻起土地来,总算得心应手了些。然而好景不长,对于工具的全新需求总在不知何时冒出来。春日一过,杂草繁茂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。只是周末出门两天,回来一看,一片绿油油的杂草如举家搬迁而至的蟑螂一般,塞满了各个角落。需要除草器。好歹应付了杂草,夏日里头树苗也来凑热闹。——不不,并非刻意栽种的树苗,而是自说自话一般长出来的树苗。柳树和榆树的种子被风吹来,桑树、构树则要靠鸟类——喜鹊或乌鸫——的粪便。望着那些不请自来的树苗,我仿佛听到风吹过的声响,以及鸟类排泄时的动静。噗嗤。 树苗不同于杂草,顽固程度简直可与脚气相提并论。若不连根拔除,便会没完没了。外出旅行一阵子回来,构树已经长到了五十厘米之高,叶片厚墩墩地展开,一幅挑衅的模样。 还有臭椿。每年都有臭椿的新苗,毕竟果实依靠风吹,轻易就会从哪里飘过来。明明拔个干净,岂料过上一阵子,又会从原地冒出头来。“臭椿嘛,除非彻彻底底连根拔除,不然是不好办呀!”经人这么一说,我也发起愁来。外星人占据地球,臭椿树占据花园,纳粹占据波兰,任哪一个都不是令人开心之事。 去年偶然遇见了“拔根器”——正式名称叫做螺旋起草器,啰嗦是够啰嗦的——即,如同红酒开瓶器般的工具,下头是金属螺旋结构,上头配以手柄。旋转着拧到土地里头去,向上用力拉拽。呼啦一声,整个小树苗都能拔出。“不得了呀,”我暗自感叹,“果然要找到合适的工具才行。”纵然一年用不上几次,但反正需要之时,总能派得上用场。 说来“拔根器”倒是虹越园艺赠送的。参加虹越的活动时,任由到场嘉宾挑选一款工具,我便看上了“拔根器”。岂料今年跑去伦敦参观切尔西花展之时,在一家摊位前,见识了各式各样的“拔根器”。彼时虹越园艺的员工,有好几个人也恰在切尔西花展现场。毕竟公司的领导者甚是目光长远,肯将员工送到欧洲,参加园艺界里头首屈一指的花展。花销怕是个大数字。但我反正已有了“拔根器”。此番在异国相遇,心里头多少有些感叹,默念了几句感谢的话语。 可惜“拔根器”亦有无可奈何之时。藏在石缝里的臭椿树,终究如雨后急匆匆的蘑菇一般,吭哧吭哧长了起来。有些木本植物就是如此让人头疼。“怎样才能彻底除去花园里的凌霄花呢?”前些日子,有人问我道。凌霄花也好,臭椿也好,都是相当麻烦的植物啊!纵使有了适宜的工具,到头来也有无法做到之事。一如我每每回想起阿尔卑斯山中的老猎人,牛排刀是给了我来着,鹿肉则到底又酸又咸,瘦肉纤维也硬梆梆的,仿佛在啃鞋刷子。这是无论怎样讲究餐桌礼仪、规范地使用刀叉,也无从更改之事。 臭椿Ailanthusaltissima 臭椿Ailanthusaltissima 臭椿的果实倘使细看来,仿佛略有些扭曲了的眼睛模样。种子即是眼球所在,两侧直到眼角,则是又轻又薄的滑翔装置——植物学里头称之为“翅”。风一吹,由翅携带着种子,反正飞去了某处。偏偏臭椿又极顽强。我家老宅楼下,曾有一棵臭椿树苗来着,我读中学时,那树约摸长到三层楼高,如今则已到了六层楼,成了树阴浓郁的一棵大树。 然而一旦生根,想要除去一棵臭椿,其难度近乎等同于水熊虫登上火星。今年春日,我在北京临着国子监后墙的院落里头,听一位朋友抱怨了一番。她将院子租了下来,打算改造为兼具花园功能的客栈。然而二层楼上,可以眺望国子监院落的位置,有一棵臭椿无论怎样砍伐,过不多时,新叶又生出来。树干与老墙融为一体,无法连根拔起。委实无法可施,唯有隔上三五日便去剪枝。“到底是臭椿嘛!”抱怨完毕,我们两人一同喟叹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pailuanjiance.com/lcnzyw/328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圆梦解梦
- 下一篇文章: 二年级语文上册全写字动图拼音部首